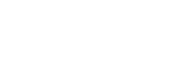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有幸邀请到访清华大学哲学系
在陈荣捷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了纪念陈荣捷先生系列活动,其中,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有幸邀请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教授为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开展主题为《朱子五讲》系列讲座。所以到访中山大学哲学系、开展“朱子”为主题的讲座,陈来教授讲述道,陈荣捷(1901-1994)先生乃广东开平人,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又曾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教务长。其著作等身,不仅在西方英语世界长期从事并奠定新儒学研究,还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资料的英文翻译与辞条撰写工作哈佛大学哲学,为中国哲学思想在海外的进一步理解和推广不竭余力,被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其中,朱子学是陈荣捷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陈来教授表示,讲座以“朱子”为主题,正是向陈荣捷先生致敬。
本系列讲座共五讲,分别于2021年4月15日、16日、17日、20日、21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以下为本系列讲座下半部分(第四、五讲)内容纪要的回顾。
四、《朱子论义》纪要
第四讲题为《朱子论义》,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主持。
陈来教授

杨海文教授
讲座伊始,陈来教授区分了秦汉以前有关“义”的两种常见解释:“以宜释义”和“以正释义”。陈来教授指出,在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一书中,有专章“朱子论仁”,但无专章“朱子论义”。近年有不少学者关注“朱子论礼”,但鲜有关注“论义”者。先秦文献中对“义”的解说不少,其中属于文字学的解释是“义者,宜也”。“宜”的本意为合适、适宜,引申为适当、应当。所以“宜”字本偏重于实然,而非直指当然。除了“以宜训义”之外,“以正释义”在战国时期已相当流行。陈来教授指出,“以宜训义”是声音相训的结果,这种训释方法使“义”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内涵不能确定。
随后,陈来教授继续梳理了汉唐注疏对“义”的两种新阐释:“裁制”和“断决”。陈来教授认为汉后“义”的新解释仍建基于“以宜训义”的理解。以“裁制”解说“义”字之义,始于《释名》,后来被各种文献广泛采用。同样,汉唐其他注疏中也多有以“断决”“断割”“断制”解释“义”的说法。汉唐注疏对“义”的解释影响了不少宋人的理解,但宋明理学对“正道曰义”的思想没有阐述发挥,仅仅突出了“仁”的价值意义,“义”的价值对“仁”的重要补充被忽视了。
就朱子对“义”的理解而言,陈来教授认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义”的训解仍旧延续“义者,宜也”的古训。从经学注疏的方法来说,朱子沿袭了《论语注疏》《孟子注疏》的注释方法,其注释并非纯义理式的说解,而是重视在训诂的基础上讲明义理。朱子所理解的“宜”,不是实然,而是应然。汉唐的注释对朱子的义理哲学产生了影响,朱子在注释义字的时候也对训诂义与思想义作了区分。朱子将“义”的理解区分为天德和人事两个方面。“义”的涵义有分别之意,相比起来,仁的涵义不是分别,而是一体。陈来教授指出朱子重视从“心”上界定“义”,《论语注疏》对“义”的训释是“以事言”,朱子将“以心言”与“以事言”加以结合,他以“宜”为以事言,而以“裁制”为以心言。
紧接着“以心言”和“以事言”的区分,陈来教授认为,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对“义”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时,主要不是用“宜”来界定“义”,而是从汉儒的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朱子还重视从伦理属性的方面去讨论“义”。陈来教授特别指出,“义”的本性是裁制,根据朱子的解释,羞恶之心根于义,其中羞是羞自己的恶,恶是恶他人之恶。陈来教授认为这个区分非常重要,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义”中羞自己之恶的面向。朱子将“义”理解为是一个面对恶的德性,“义”的属性就是面对恶时,要清楚判别善恶、憎恶不善,然后果断去恶,这就是裁制之意。朱子对“义”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孟子把羞恶与“义”连接起来的影响。

陈来教授特别指出,朱子把“义”解释为“断制”有其独特的意义。朱子用“断制”来解释“义”的价值特性,“断制”二字是断决裁制的简化表达,强调面对恶要态度决然,除恶要断然施行。但是以断决解释“义”,削弱了“义”的价值引导意义。另外,朱子认为,能不能有“断制”,与人的性格性情有关,而性格来自气禀。朱子论“义”另一个特点,正如其论“仁”一样,是把“义”的讨论置于宇宙论框架之中,使“义”具有大化流行论的意义。朱子认为“义”在表面上似乎是不和,其实却是和。因为“义”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这正是为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常常有把仁和义对举的例子,标示出它们各自的价值特性与价值意向,朱子也是这样。
此外,陈来教授认为,以“断制”释义在朱子学中具有宇宙论意义。朱子论“义”多就宇宙论来讲,而不是专就伦理学来讲,这与朱子的整个四德论是一致的,在朱子晚年的《玉山讲义》中也有明确的体现。朱子以刚、柔来区分“仁”和“义”,但“仁”、“义”的刚柔区分要具体看是从体上说还是从用上说。朱子主张“仁”是体刚而用柔,“义”是体柔而用刚。也就是说,在体上说,仁刚而义柔;在用上说,则是仁柔而义刚。综合来看,朱子以仁、义在天德之自然的意义为体,以仁、义在人事之当然的意义为用。朱子晚年之所以强调仁刚义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子以“仁”为体的的本体宇宙论已经形成。“义”的刚柔阴阳特性哈佛大学哲学,要从整体的本体宇宙论的架构中来定位,而不能仅仅从“义”的伦理价值功能来确认。陈来教授认为,从这一点来看,朱子对“义”的处理与其对“仁”的处理是一致的。
最后,陈来教授总结了“义”的哲学意义。“义”在先秦时代主要有道德,道义、正义、善德、端正几种意思。而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在于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这是对先秦“以正释义”思想的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突出“义”是对不善的憎恶。朱子对“义”的哲学理解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的论“义”的裁断义,二是把“义”纳入以仁德为首的四德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陈来教授指出以裁断解“义”未能突出“义”的价值内涵;但另一方面,“义”的裁断义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问答环节
现场学生:朱子说“盖仁多,便遮了义;义多,便遮了那仁”,如何理解朱子思想中仁与义的关系?仁与义是否会相互冲突?
陈来教授回应:朱子说的仁义礼智四德是一体的,不可孤立看待,其中仁主发生,义主断制,义礼智皆是仁的不同面向。
在本场讲座即将结束之际,陈来教授不辞辛劳向在座师生分享自己近日在潮州参观韩文公祠和薛侃家庙等的所见所思。陈来教授认为被称为海滨邹鲁的潮汕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文脉传承,如韩愈所代表的文章之道,除此之外,还有一脉儒教传统也在潮汕地区流传不息。陈来教授指出儒教传统亦是文教的传统,代表着道的传承。
五、《朱子论羞恶》纪要
第五讲亦即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题为《朱子论羞恶》,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主持,这也是陈来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学活动的尾声。

陈立胜教授
讲座开始,陈来教授介绍道,《朱子论羞恶》可以看作上一讲《朱子论义》的续章,但同时也打开新的问题面向。在儒学体系中,“羞恶”一词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羞恶既是义的发端,也是四端之一。羞恶的问题既与义相关,也关涉到四端的讨论。因此以羞恶为焦点来展开讨论,一可以厘清羞恶在历史上模糊的含义,二也可以通过对羞恶的讨论来加深对义的理解,三能进一步拓宽对朱子心性学的理解。
陈来教授的首个关注点,落在从性情体用、已发未发的角度阐述羞恶作为义的发端。统体而论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有幸邀请到访清华大学哲学系,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恻隐、羞恶等为已发之情。就二者关系而言,四德之性是四端的根子,四端之情是四德的表现。也就是说性不可见,惟在情之已发时可见,因而人就可以从已发之情来内推未发之性,这属于认知本性的方法。
在讨论了羞恶的内在根源后,陈来教授从羞恶的外在原因出发,论述羞恶之心是由不善、可恶之事所引发。以仁义对言,仁体现为好善,义体现为恶恶。以羞恶对言,羞是耻己之不善,恶是憎人之不善中山大学禾田哲学讲座有幸邀请到访清华大学哲学系,前者重在自己,是从修身的角度说,后者更重他人,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从四德整体看,专言之仁可以包四德,仁的生意贯穿于四端之间。因此在四端发见时,如果对事物首先没有表现出知痛痒、能恻隐,也就不会有羞恶。也就可以说,羞恶是生意的一种表现,是生意遇到可恶之事便表现出了羞恶的“面貌”。另外,陈来教授补充到,舍勒关注的羞恶问题与儒家讨论的羞恶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
在论述性情关系后,陈来教授引入了气禀的问题,从其对性理发见的影响而言,则有羞恶其不当羞恶者。朱子对四端的理解有广狭之别:性理直一而发、全然而善的情感属狭义;性理堕在气质中发见而有中节与否的情感属广义。这种区分是基于理学心性思想发展的需要。
从气质一面而言,虽然天命之性人人全具、未尝有偏,但气质所禀却有昏明厚薄之不齐。以义为例,义德与人所禀受的清俊刚烈的金气有关。人禀得此气多,就会更多地表现出断制,但也随之可能表现出羞恶其不当羞恶者,乃至于以一端遮蔽其他端绪的发见。陈来教授认为,在《孟子》和《中庸》之间,孟子重在论述四者人皆有之,但因初发时细微,所以要扩而充之;《中庸》却重在论述四端之发有中节与不中节的不同,而朱子的工作,是将四端观念抽离《孟子》的文本,扩展为广义的包含了善恶的四端观念,这与现实情形更加相符。在功夫上,朱子主张要“于其发处,体验扩充将去”。
从《孟子》四端说到《中庸》四情说,朱子思想前后期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性情体用转变为对心的讨论,这就将四端问题关联上了人心道心的问题。对此,陈来教授辨析道,道心是道德意识,人心是感性欲念,二者都是人的知觉之心。中节全善的四端是道心,广义的四端却不能说是道心。就心、性、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性是理,情是流行运用处,而心是具此理而行此情的。在性情关系中加入心的维度,凸显了心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主宰作用。但朱子前期所讲心主性情更重在心性情结构,只有心为主宰义与道心人心说结合之后,心的道德实践的意味才被显明,从而超越心统性情的结构意义,因此朱子在后期对心的主宰作用的强调,更具有功夫论层面的实践意味。最后,陈来教授总结到,孟子的性情说与《中庸》的中和说构成重要的互补,而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揭示出,对于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处理,只有性善论是不够的,必须有持中的实践范导和裁制,思想感情的活动才能中节而善。
演讲过后,陈立胜教授首先重新梳理、总结了陈来教授的讲座要点,又向陈来教授提问,如果说仁是好善,义是恶恶,是非之心是否统摄了二者?陈来教授答道:是非之心强调对是非的辨析,不包含实际好恶的方面。但良知就不仅是对是非的明辨,也包含好善和恶恶。阳明在南赣时期也强调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到晚期的使用范围则有所扩大,将良知主要落在真诚恻怛一面来说,其实体现得更多的是恻隐。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提问道:“端”的含义在孟子处是萌芽、发端,即由羞恶之端可以发展出义,但在朱子说因羞恶而知其有义,方向却是反过来的。朱子和孟子的思路是否完全颠倒?陈来教授答道:朱子更强调从认知的角度由已发回推未发,孟子却没有这个面向,而更强调如何从“端”这里推扩出去。朱子虽然也讲扩充,但不如孟子作为核心观念那么重视。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庞令强问道:四端之中,“羞恶”、“是非”、“辞让”每个词中的两个字都具有独立的含义,但“恻隐”两字却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恻隐之心和其他三端就似乎是一和三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这会不会对伊川、朱子以专言和偏言看待四端(四德)的观点构成挑战?陈来教授回答道:这应该构不成挑战。专言说的是仁包四德,偏言说的是一个是一个。仁包四德有整个宇宙论的背景,但你所说人己、内外关系并不会影响宇宙论模式。而且一对三也不是绝对,有很多分类方式,如仁义、仁礼、仁智都可以分别对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罗慧琳,接着陈老师向外扩充和向内识仁的问题追问道:如果四端有中节与否的区别,那么一个不中节的端绪怎么向外扩充?由此向内识仁体又何以可能?陈来教授回答道:扩充也不仅仅是向外的,先体认发出来的情感,然后将发得对的这些情感进行扩充。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老师问道:在性情体用的关系上,理学和心学的区别在哪里?朱子思想前后期的分别,有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种转变?后期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哪里?陈来教授回答道:朱子从已发来回溯未发并不能将此归结为即用见体,反而朱子更重视立体。而心学不重视分别已发未发。清人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比较粗疏,一般只落在功夫大旨,在他们看来朱子在四十岁以后思想就没有变化了。二十世纪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更细致,但仍有待于推进。我今天讲的大概可以概括为三阶段,心统性情是在四十岁到四十四之间,属中前期,朱子从四十八岁之后,对《四书》下了更多功夫,而人心道心问题是在五十九到六十岁,这个时期可以作为朱子晚期思想的代表阶段。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问道: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是否存在故意曲解的可能?如果朱子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为什么不单独论说,而是要附加在《太极图说》上?二程不提周子,反而朱子明确表彰,这其中有什么意味?陈来教授回答道:周子是否重在讲气,仍然是不明确的。在朱子以前,周程之学已经成为显学,二程的弟子比朱子更早表彰周子,这也表明二程思想有所传承。当朱子时,周子已经作为二程的先导者出现,这个形象引导了朱子的诠释。从周子思想本身看,他仍然是延续儒家《易》学传统,并非道家思想,从“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可以看出来,而他独特的贡献在于揭示出精妙、简明的宇宙论体系,为朱子所尤其重视。朱子当时的学者也并没有对《太极图说解》提出大的反对,即便是陆九渊也没有对整个体系发出质疑。而二程之所以不再往下传,在于没有可传之人。西方哲学在传承中,后人总是挑前人的毛病,中国哲学却不同,后人总要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养分。
至此,陈来教授此番中大讲学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片:罗慧琳)